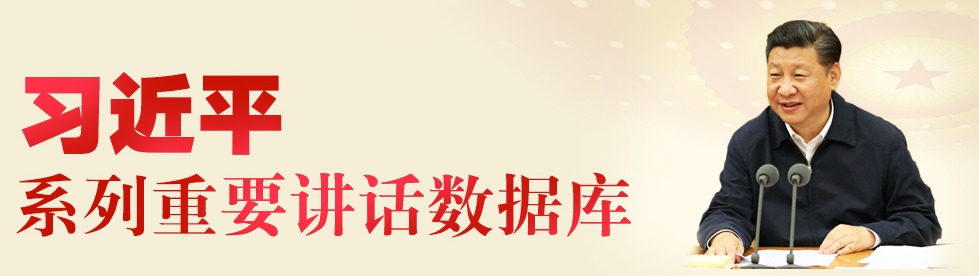2025 年 8 月 12 日,天津港大爆炸迎来十周年。当年那场夺走 165 条生命(含失联者)的灾难,在幸存者心中刻下的伤痕,从未真正消失。近日,一位化名 “老周” 的幸存者在社交媒体发布长文,回应多年来围绕自己的 “苟且偷生” 争议 —— 有人曾质疑他 “既然活下来了,为何不拼尽全力追责”,也有人不解他 “为何能如此平静地过普通人的生活”。这篇文字揭开了幸存者群体在十年间的心理挣扎与成长:** 平静不是遗忘,活着本身就是一种责任。**
老周是当年爆炸核心区某物流公司的夜班调度,爆炸发生时他被气浪掀飞 30 米,右腿粉碎性骨折,昏迷 72 小时后获救,但同办公室的 5 名同事全部遇难。“醒来后看到新闻里的死亡数字,第一个念头是‘为什么死的不是我’。” 这种幸存者内疚(Survivor's Guilt)成了他最初几年的心理枷锁。
争议始于 2018 年,有遇难者家属在纪念活动上情绪激动地指责部分幸存者 “只顾自己疗伤,忘了谁该为悲剧负责”,老周因当时拒绝参与公开维权活动,被贴上 “苟且偷生” 的标签。“不是不想追责,是身体和精神实在扛不住。” 他回忆,术后三年里,他每天要吃 6 种药控制创伤后应激障碍(PTSD),夜晚反复梦见爆炸火光,听到警笛声就浑身发抖,“连下楼买瓶酱油都需要妻子陪着,哪有精力去‘拼’?”
外界的误解往往忽略了幸存者的创伤困境:据天津安定医院 2016 年的调查,爆炸幸存者中 78% 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,其中 43% 有睡眠障碍,29% 出现回避行为(拒绝谈论爆炸、避开事发地周边)。“我们不是‘遗忘’,是身体在强迫我们‘暂停’,否则会垮掉。” 老周说。
老周的 “平静” 并非一蹴而就,而是一场漫长的自我救赎:
- 物理空间的迁移与回归:2017 年,他随家人搬到天津郊区,刻意避开所有可能触发回忆的场景。但 2020 年,他主动搬回了距离事发地 5 公里的小区,“躲了三年,发现越躲越怕,不如试着面对”。如今他常去附近的公园散步,路过当年重建的物流园区时,会驻足看一会儿,“不再发抖了,只是心里会空一下”。
- 日常细节的疗愈力量:他学会了养花,阳台摆满了同事生前喜欢的月季;每天接送女儿上学时,会特意绕路经过当年救治他的医院,“看到门口的救护车,不再联想到爆炸,而是想起救过我的医生”。这些琐碎的日常,成了他与创伤和解的 “锚点”。
- 心理干预的支撑:前五年,他坚持每周接受心理疏导,从最初的沉默抗拒,到后来能平静讲述爆炸瞬间。“医生说,‘活着’本身就是对生命的尊重,不需要用‘追责’或‘痛苦’来证明自己没有忘记。” 这句话让他逐渐放下了自我苛责。
老周的 “责任”,藏在不被注意的细节里:
- 一份持续十年的名单:他的手机备忘录里,记着 5 位遇难同事的生日。每年这天,他会带着他们的照片去海边(其中 3 人喜欢看海),摆上他们爱吃的零食,“跟他们说说家里的事,比如我女儿考上了重点小学,就像他们还在身边”。
- 一场面向孩子的安全课:2022 年起,他加入了社区 “安全宣讲队”,用自己的经历给中小学讲危险品安全知识。“不讲爆炸的惨烈,只说‘遇到危险该怎么跑’‘为什么不能在危险品仓库附近玩耍’。” 他觉得,让活着的人学会保护自己,比反复控诉更有意义。
- 对遇难者家属的默默陪伴:他和另外几位幸存者自发组成了 “互助小组”,每年 8 月 12 日会去纪念碑献花,也会在遇难者家属情绪低落时上门坐坐,递杯热茶,不说太多话。“我们不劝‘放下’,只告诉他们‘我们也记得’。”
正如老周在文中所写:“有人说‘活着就要讨个说法’,但对我们来说,‘说法’重要,‘活着’本身更重要 —— 活着记住教训,活着保护更多人,活着让那些离开的人,以另一种方式‘存在’。”
十年间,社会对幸存者的态度也在悄然转变。最初,舆论更关注 “追责”“赔偿” 等显性议题,对幸存者的心理需求关注甚少;而现在,越来越多人意识到:** 灾难后的 “活着”,本身就是一场需要勇气的战斗,幸存者的平静不是妥协,而是对生命最坚韧的回应。**
天津社科院社会心理学研究所研究员李静认为,老周的故事折射出幸存者群体的普遍成长:“从‘被创伤定义’到‘定义创伤的意义’,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了对生命的交代 —— 这不是苟且,是另一种形式的勇敢。”
十周年的风,吹过重建后的天津港。老周站在纪念碑前,轻轻抚摸着墙上同事的名字。阳光落在他脸上,没有泪水,只有一种历经沧桑后的平静。“他们没走完的路,我们替他们走下去。” 这句话,或许就是对 “苟且偷生” 争议最有力的回应。
(责编: admin1)
免责声明:本文为转载,非本网原创内容,不代表本网观点。其原创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,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、文字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,请读者仅作参考,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。